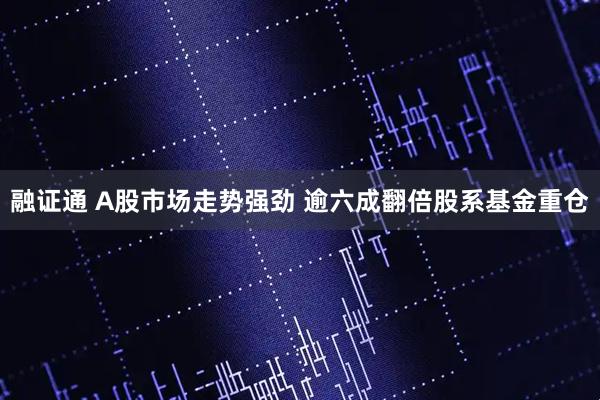*本文摘自《厦门文史资料》第十四辑(1988年11月)万店优配,作者余钟民,原标题《我在厦门警察局长任内的见闻》
图片
图片
一九四八年九月,国民党中央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纵来闽视察,他要我到厦门担任警察局局长。据说,是他与刘建绪讨论加强福建地方团队和警察的组织与训练时,刘建绪提出厦门警察局长谢桂成庇护军统人员、流氓在地方上为非作歹,引起了华侨和社会人士普遍的不满。因此,决定改派我继任局长。我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到厦门任职,至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派其副侍卫长刘树梓来厦接任为止。我在担任警察局长期间,对于厦门社会的黑幕,较为了解。现就我回忆所及的写出来,以供参考。
一、厦门社会的黑幕
抗战胜利后,厦门人民欢喜若狂,他们在日军长期蹂躏的苦难中挣脱出来,满以为从此可以得到安居乐业。谁知自国民党接收厦门后,横征暴敛,贪官污吏敲诈勒索,地方派系明争暗斗,军政人员、流氓地痞走私贩毒、抢劫绑票、打架闹事种种罪行,馨竹难书,下面只是个人了解的部分情况。
1、走私活动
抗战胜利以后,厦门的走私活动极为猖獗。当时,市场上美货充斥,大都是由菲律滨、香港等地走私而来。走私进口货物的品种繁多。如:呢绒哔吱、卡机布、人造丝绸、玻璃制品、塑料、食品罐头、烟、酒、西药、巧克力糖、黄金、军火、及鸦片、吗啡毒品等。这些美货都是通过军、宪。警人员、流氓勾结走私商人,以各种方法走私进口的。
武装走私
武装走私,是一种主要的走私方法。武装走私者在香港租用外国货轮,直接装运货物,走私进口。船到厦门,即由流氓武装保护卸货。例如一九四七年,在斗西码头暴露武装走私大案一起。(编者按:斗西码头武装走私大案详细情况,本刊在一九八六年第十一辑第86页至第88页已刊载,故略。)
有的走私商人,事前与军、宪、警、流氓勾结好,经常往来于香港、厦门之间,搞走私活动。他们把私货打成行李包,船到厦门港口停候海关检查时,即有武装的小汽船驶靠外轮,将私货迅速地卸下运走。海关检查人员即使看到,亦只是装聋作哑,不敢过问。反正海关人员也与他们有勾结,大家心照不宣,彼此相安无事。此外,还有特务、流氓备有专用的小船或机帆船进行走私活动。如军统人员张廷标等人,即备有机帆船一艘,船上配有武装的流氓数人,经常川走台湾、厦门之间进行走私。
在厦门执行进出口船只检查的,有海关、宪兵、水警等几个单位。检查人员勾结商人走私,在当时可说是公开的秘密。其走私方法多种多样,如有的走私商人,事先与检查人员勾结好,在检查人员上船,尚未执行检查时,将体积较小的私货,如高价的西药或黄金等,直接交给检查人员携带上岸。一般的条件,是照实物的价值送百分之十给检查人员,这在当时称为“保险走私”。另一种是检查人员与商人合夥走私,资本多出自商人,所获利润,一般是四、六分成,即商人得六成(或三、七分成)。走私方法,是将私货装成大行李包。按当时海关规定,普通行李包经检查后,一律课以轻税放行。海关检查人员,如遇有勾结的私货“行李”,仅马虎地检查“一番”就在行李包上用粉笔划一个检查记号,即被认为是经过检查课税等手续,可以通行。这种方法,以勾结海关检查人员为主,因为行李课税必须经过海关人员签字,才能通行。也有的商人直接与宪兵或水警检查人员勾结,通过他们向海关检查人员关照一下,亦可通行无阻。这种勾结某一方面的关系,当时叫做“单线”关系。但“单线”关系并不完全保险。虽然,海关、水警、宪兵的检查人员,各有各的路线搞走私,一般来说,彼此可以保持默契,互不侵犯。但有时走私商人,对某一方面应付不周到时。也会出问题。例如:一九四八年,有某走私商携带大“行李”多件,虽经过海关签字放行,而水警因未分沾油水,当“行李”运上码头时,水警拦住检查。查出贵重西药一大批,即将人货一并扣留。海关人员恐怕案情暴露,多方托人向水警大队疏通。结果,水警大队只好把扣留的私货移送海关处理。后来,海关仅以补税了事。但此中私货,已被水警吞没了大部分。此外,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之后,按当时的中央银行规定,旅客向海关缴税一律以金圆券交付。该行每于外轮进口时,即派人随同海关人员上船,办理黄金、外币兑换。海外归国华侨所携带的都是黄金、外币,他们在船上要以金圆券缴付税款,不得不以黄金和外币来兑换。可是当时黄金、外币的黑市价格与中央银行的兑换率相差甚巨。于是有些地下钱庄与检查人员勾结,派人携带大量金圆券,随检查人员上船,暗中以高于公价的价格,向旅客收购黄金、外币。转手之间,即可获得巨利,再与检查人员共同分肥。
船员走私
厦门与香港和南洋各地往来的外轮,每周常有两、三艘。这些外轮的船员,从船长到水手,无不走私。他们所带私货,数量不大,易于处理。每当轮船进口,客货卸下之后,他们在夜间雇用小船,偷运上岸出售。当时有流氓设在码头一带的“窝户”,俗称“海鸡母行”,专门收购船员的私货,用现金交易。其收购价格,一般低于市价一倍左右,买卖双方均称方便,尤其是买方转手之间即可获利。这些“窝户”每当外轮进口后,即派人上船,向船员兜揽生意。各“窝户”竞相抢购,打架闹事,冲突火拼之事,时有所闻。
军火与鸦片走私
军火与鸦片、吗啡等毒品,是走私进口的主要品种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大量低价抛售菲律滨等地的剩余军火,一支美制短枪,不过三、四美元。而厦门当时价格短枪每支五、六十美元。在厦门及内陆各县,军火几乎可以公开买卖,并形成了一定市价。一支下壳枪值美钞二百元或黄金四两;一支大曲七枪手值美钞一百元或黄金二两;卡宾枪价与卜壳枪相等;一支汤姆生轻机枪值三、四百美元不等。因此,军火走私曾盛极一时。因走私商多与特务或军警机关勾结,所以平时破案极少。仅在一九四八年十月间,有一次例外。警察局在荷轮“芝巴德”轮船上,查扣某华侨与宪兵连勾结,走私进口一大批军火,计美制短枪一百四十多支,价值美钞七八千元。警察局查扣时,与宪兵连发生冲突,几至火拼(详情下面还将谈到)。当时也有少数归国华侨,为了自卫而携带两、三支短枪进口。水警大队从归国华侨中,查扣零星短枪,累计起来数量不少。
至于鸦片、吗啡等毒品走私,大多来自香港。当时,厦门及内陆各县烟馆林立。鸦片来源,多由走私进口。其走私路线,除直接由外轮运进以外,大批的走私则由香港偷运至汕头,再用木船转口运来厦门。因为木船到厦门,随处都可停泊,易于逃避检查。一九四七年冬,厦门水警大队偶而查扣一起走私鸦片。某日,夜十时许,一个水警在码头巡逻,发现海边停靠 木船一只,船上装有肥皂数十大箱。查问货主时,却无人出面承认。水警认为可疑,把木船扣到水警分陕部,切开肥皂检查,发现每块肥皂中间夹装“福字”鸦片烟膏四小盒,数十大箱的肥皂,块块都有夹装,数量十分惊人。据当时水警大队督察员董蒙正谈,这些鸦片扣留后,由分队送到大队,层层吞没不少。
2、抢劫、绑票
抗战胜利后,厦门地方秩序最为混乱,抢劫和绑票案件,经常发生。被抢劫的,大多是金店和殷实华侨。据警察局当时的统计,厦门市内所发生的抢劫案件,平均每月不下二、三起。厦门是一个小岛,发生抢案本来容易缉获,但行劫的匪徒,多与流氓和特务有关,每当抢劫过后,均可得到庇护而安然逃走。据了解:当时到厦门行劫的匪徒,抢劫得手,即由特务、流氓保护,坐小船逃走,警案局几乎无法破案,即使偶尔抓到一、二个匪徒,当警察局将案移送法院之后,经特务向法院打通关节,均可以轻刑判处,转到监狱后,不出数月,便可因病保外就医,或“越狱”脱逃。实际上,是买通狱吏,将犯人私自放出,而后向法院报告“越狱”在逃了案。
3、陈、吴、纪三姓的械斗
厦门码头,有陈、吴、纪三姓封建把头势力。他们为害地方,十分严重。尤其在抗战胜利后,特务、流氓打入“三姓”,从中兴风作浪,纠纷时起,以致武装冲突,流血事件层出不穷。解放前,厦门的码头工人多为同安县籍,其中以陈、吴、纪三姓占绝大多数。他们在封建把头的控制下,形成三大封建势力。经常为争夺码头而发生械斗,结下冤仇。陈、吴、纪三姓在厦门各有宗祠,月由工人劳动所得,抽取会金,购置长短枪支,并积累了大量基金,备为一旦发生槭斗时的诉讼等费用。操纵吴姓家族组织的,是与军统有关系的吴在善(陈、纪两姓的把头姓名已忘记)。这些把头经常借端制造纠纷。一九四六年秋,我任福建省水警总队长时,吴、纪两姓曾为了争夺轮船卸货而发生械斗,互相开枪射击。一时码头混乱,船上旅客哀声惨叫,混作一团。经水警大队出动大批武装员警到现场弹压,始得以制止。结果,双方枪伤十余人,而纪姓重伤致死者一人。我得到厦门水警大队的长途电话报告后,赶到厦门。据报双方继续酝酿再打,当即召集吴、纪两姓头头吴在善等十余人,在水警大队部进行调处。我首先要双方交出肇事凶手和武器,同时,要他们具结,保证此后不再发生械斗,并拟订了解决办法数条。征求双方同意后,由水警监督实行。他们对解决办法,都表示同意,但不肯交出凶手和武器。我当时大施压力,申言如不照办,即扣留双方负责人顶替凶手,依法送法院处理。经这么一威吓,他们才答应照办。双方各交出凶手二人和卜壳枪两支,并具结保证不再发生械斗。后来,水警大队将全案移送法院处理。
4、船只检查与勒索
厦门是福建华侨唯一的进出口岸。抗战胜利后,南洋各地的华侨归国,络绎不绝。当时,常川南洋各属与厦门间的外轮有:芝沙丹尼、芝沙连加、万福士,芝巴德、李庆等七、八艘,其中芝沙丹尼、芝沙连加都是万吨以上巨轮。此外还有侨资的“太平轮”,但只二千多吨。这些航班大都客货满载。据厦门水警大队的统计,当时进出口的华侨,每月约达万人左右。厦门进出口船只的检查,最初没有统一规定,除海关以外,几乎所有军警单位,都上船检查。如宪兵、水警、海军、警备司令部等等。每当船只进港,大批的检查人员及特务、流氓,蜂拥而上,对旅客进行反复检查,翻箱倒柜,借端敲诈,无所不为。再加上封建把头的勒索:他们抢卸行李,任意索价,每件行李索价高达二、三美元。遗失行李的事件万店优配,也时有所闻,旅客怨声载道。一九四七年春,我随刘建绪到厦门视察时,各华侨团体纷纷向刘建绪控诉,提出整顿码头秩序的要求。刘建绪要我拟订一个“统一检查办法”,规定对进出口船只实行统一检查:限定以海关、水警、宪兵三方面为检查单位,其他军、警机关都不准上船。检查行李、货物以海关为主,宪兵、水警会同协助。对每一旅客,只检查一次,不得重复。在统一检查未完毕前,任何人不准上船。同时,规定卸运行李以及渡船的统一价格,严禁抬高索价,否则,由水警负责取缔等等。刘建绪召集有关单位开会宣布“统一检查办法”,要求严格执行。自后,进出口船只的混乱情况,稍有改善。但检查人员对旅客的苛索,仍无改变,并且给他们勾结商人走私带来了方便。
5、中统与军统的明争暗斗
厦门地方派系的斗争,抗战胜利后尤为剧烈。国民党C C派与三青团,军统与中统之间,争权夺利,从市级单位到区、镇,从行政到公共事业和参义会各方面,可以说“遇事必争,无孔不入。”他们在接收厦门的过程中,不但劫夺了大批的敌伪产业和物资,发了“胜利财”,而且将他们的魔爪,伸展到每个角落,形成了地方的两大恶势力集团。
属于中统的势力范围,有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长黄谦若,CC派厦门负责人),厦门市政府(市长黄天爵):市商会(会长严焰)、市参议会(议长陈烈甫)、市总工会(主席龚金水)中央日报(社长郑善政)、南侨通讯社(社长吴春鉴)、中央通讯社(特派员冯文质)、城内和草仔垵流氓集团以及市党部、各区公所、工会等单位的行动队(便衣特务)等。属于军统控制的单位有:闽南站(站长王兆畿)。闽南站后改为闽南组(组长庄尚德),三青团分团(干事长郭薰风)、市警察局(局长先后是沈觐康、徐步奇、谢桂成、余钟民、刘树梓)。水警第二大队,(大队长王福青)、水警大队后改为厦门水警分局(分局长刘长泗)、立人日报(社长王兆畿)、青年日报(发行人郭薰风)、中国经济通讯社(社长吴贞),经济通讯周报(社长吴贞)以及和凤宫、关仔内等流氓集团。一九四六年,福州成立中国新经济建设协会时,厦门各派流氓势力都被拉入该会厦门支会中,由军统重要人物吴贞负责领导。中国新经济建设协会系军统所控制的流氓组织,总会设在上海,上海青红帮大头子杜月笙、黄金荣、王晓籁等为主要负责人。军统派·徐为彬为该会书记,操纵着整个组织的实权。不久,这个流氓组织到处闹事,蒋介石下令取消。厦门支会取消后,吴贞暗中另组织了一个“仁社”自兼社长,继续控制着这批流氓势力。
中统与军统明争暗斗的丑剧,从抗战胜利至厦门解放时,一直演个没完,下面谈几个较为突出的事例。
市参议会议员的争夺战
一九四六年厦门市第一届参议会的选举,是中统、军统两派斗争最剧烈的一个场面。他们在各个选区里,都提出候选人参加竞选。选举前,两派都派有大批打手、流氓,在各选区进行拉票,闹得乌烟瘴气。其中以鼓浪屿笔架山选区,
军统候选人张圣才与中统候选人陈烈甫争夺最为剧烈。陈烈甫是中统方面内定的市参议会的议长候选人,势在必争。所以中统动员所有力量,支持陈烈甫竞选。而张圣才声称要建立国民党“反对派”,写了许多文章在《江声报》上发表,颇引起某些社会人士的注目。正式选举之日,军统、中统两方出动大批流氓打手,各携带武器,准备厮杀。警察局鉴于情势严重,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派出武装员警到现场监视,总算没有打起来。选举结果,张圣才当选,张烈甫落选。后来,中统只好用临时增加名额办法,把陈烈甫选出来,并当上了议长。
争夺思明戏院
思明戏院是厦门最大的一家影院。抗战胜利后,由中统方面接收,並组织股份公司经营,获利甚多。军统方面看了眼红,指使张廷标为头的一批特训班学生出面抢夺。张廷标等找到原思明戏院的业主,订定了合约,于一九四八年秋,向中统方面提出接手经营,中统方面当然不让,张廷标便纠集一批流氓打手,各携带武器,忽于某日下午,把思明戏院强行占领。中统方面,亦集合不少特务武装,准备反扑。一时情势紧张,戏院附近一带的商店赶忙关门闭户,如临大敌。我接到报告后,马上派督察长王福青率保警队到现场,会同思明分局弹压。我把张廷标请到警察局来,对他说:“强占思明戏院是非法行为,警察局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当然要取缔。你这样做,不是和我为难吗?希望你顾全大局,马上把人撒出来,而后我派人负责从中调处。”张廷标过去是我的旧属,与我有一定感情。他见我态度坚决,只好回去把人调出来。至此,一场火拼暂告停止。后来,我派督察长王福青从中调解,帮他们“分赃”。结果,中统方面就思明戏院的股份拨出一小部给张廷标这伙人,彼此和解了事。
大华饭店的争夺
大华饭店是沦陷时期日籍浪人所经营的一家规模较大的旅馆,内部附设有菜馆,舞厅、赌场以及露天花园等等。接收厦门时,军统抢先占住,CC派方面想抢过去,就由国民党市党部出面,以办“社会服务处”为名向军统交涉。军统则坚决不让,两方面相持不下,CC派方面企图以武力接收。军统闻讯,亦组织了大批流氓打手,准备以武力对抗。一时闹得风声鹤唳,附近居民惶惶不安。后来,由于黄天爵怕事情闹大对他不利,因此,CC派方面只好罢手,仍维持现状。
二、我在警察局长任内的活动
1、接任初期的情况
一九四八年七月我接任厦门警察局长时,深感内外环境复杂,颇难应付。我只带两个事务人员,可说是单枪匹马赴任的。警察局的警官多数是省派的,派系复杂,问题很多。我接事后,很想先从内部人事着手,加以整顿,但由于自己没有干部基础,一时不好轻率从事。仅仅把督察长练友三换掉,改由我的旧部原晋江水警分局长王福青继任。练友三是“闽警”派系中的头目之一,我之所以敢于撤换他,主要由于他在督察长任内利用职权,经常走私活动。每当外轮进口,他即亲往码头,接运私货。他这样明目张胆的做法,连他们“闽警”同学,亦多不满意。正好这时,练友三被人告发,省政府转令市长黄天爵查办。不知是什么原因,黄天爵把它压下来,迟迟没有查复。当我向黄表示想整顿警察局内部时,他才把案卷拿出来。于是,我马上决定把练友三撤换了,借此稳定我的领导地位。
对外来说,警察局的地位处于中统与军统之间,双方都得应付的。我虽属军统人员,但我对军统重要人物吴贞等这些“地头蛇”的横行霸道,亦不满意。我接事之初,吴贞他们就想夺取警察局的刑警队。一旦刑警队被他们抓到手里,那么,他们搞走私、贩毒等种种非法活动,就可以得到更大的方便。吴贞和我早有私怨。一九四三年,他任省政府调查室主任时,由于我在戴笠面前“奏了一本”,把他调走。自后他一直怀恨在心。我这次到厦门,他一反故态,大力拉拢我,特别在鼓浪屿他的家里,为我大请其客,并举行舞会。这么一来,更使我对他怀有戒心。果然不久,吴贞想介绍陈连茂(陈达元的堂弟,军统特训班学生),接任警察局刑警队长,希望我能同意。我婉言拒绝,说我刚来接事,首先要稳定干部的情绪,目前不便更动人事。不久,有人告诉我吴贞对此很不高兴。一个月后,军统主要人员连谋来到厦门,吴贞、王兆熊等举行公宴,也约我作陪。宴罢,吴贞约我和连谋到小房间里谈话,企图利用连谋对我施加压力,要我把刑警队长宋子岑换掉,改派陈连茂接充。我当时表面上满口答应,要连谋直接打电报向保安司令部警保处处长童维经提出来,他们很满意。但我马上给童维经密告上述经过情况,并坚持刑警队长暂不更动。结果,连谋长去电保荐陈连茂,便杳无消息。自后他们打消了夺取刑警队长的念头,但吴贞对我的仇恨更加深化。
对中统方面的关系。我到厦门后,曾和黄天爵坦率地交谈,表示愿意与他合作,把厦门的地方秩序搞好,不管哪方面的人,凡是破坏地方秩序,如流氓包烟、包赌和打架闹事等等,我坚决站在政府的立场,严加取缔。希望中统方面能够谅解,并对手下的那些“喽啰”有所约束。黄天爵对我的坦率态度,似乎很同情,也表示绝对支持我,答应转知中统方面注意。后来,我在整顿地方秩序过程中,尚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我的前任谢桂成是军统闽南站派系的人物。他任警察局长时期,对军统头子陈达元、吴贞这般人可说是言听计从。他对军统大、小人物的走私、贩毒等非法活动全力庇护,且瓜分某些利益。我接任局长,谢桂成当然不痛快。陈达元、吴贞等人,也以我不如谢听话而心怀不满,甚至想方设法来对付我。例如:我到厦门不久,曾发生少数新闻记者对我大肆攻击的所谓“封锁新闻”事件。后来了解,正是吴贞等人在幕后策动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在接事之初,看到每日出入警察局的闲杂人员很多,他们不通过传达室,就直接到各科、室和办事人员坐谈,并且随意翻阅文件。我找主任秘书汪锡祺查问时,始知是各报馆或通讯社的记者采访新闻。据说,这种“自由采访”方式一向如此。我对此感到十分惊异!这么一来,警察局办理案件还有何机密可言?难怪警察局日常处理案件,往往还没有送给我,就先见报。于是我下令禁止新闻记者直接向各科室采访新闻,决定由秘书室汇集每日新闻材料,统一发布。可是,当我的手令下达各科室的翌日,《江声报》和《立人日报》等即以警察局“封锁新闻”的大字标题,歪曲报道统一发布新闻消息,並对我大加攻击。同日,记者联谊会开会,有人提议,要对我“一致声讨”,并采取一致行动,实行“反封锁”,即各报一律不刊登警察局的任何新闻。但大多数人则主张先把情况弄清楚后再作考虑,并推出中央通讯社特派员冯文质先找我了解。我把手令原稿交给他看,并说:“事实很明显警察局不但不是封锁新闻,而且是为了记者们采访的方便,还规定统一发布新闻。我对这种歪曲事实、攻击个人的报道全不在意。自然,为了自卫,我也得注视情况的发展。”冯文质与我有师生之谊,他老实告诉我,此中只有《江声报》和《立人日报》的两个记者(忘其姓名)从中鼓动。据说,他们与谢桂成、吴贞都有关系。经冯文质这么一提醒,倒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在《江声报》上发表警察局封锁新闻的当天晚上,华侨黄超群约我晚餐。餐后,在他家里举行小型舞会。不料在第二天,《江声报》的晚报《厦门大报》即登出这条“新闻”,标题是“警察局长余钟民昨晚在某处婆娑起舞”,对我大肆攻击。我看到这条消息很诧异。我想当晚只有我和谢桂成夫妇几个人,记者怎会这样“神通广大”呢?经冯文质一提,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和“得罪”谢桂成、吴贞他们有关系。后来,从军统人物张天昊谈话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冯文质了解情况后,认为我有必要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以解释误会。我接受冯的建议,在警察局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当日,各报及通讯社记者二十多人到场,我先把统一发布新闻规定的手令原底,交大家传阅。接着,详细解释统一发布新闻的用意。而后自我吹墟一番,说我来厦门,不是为了“做官”,而是想为地方“做事”,表示要对流氓、地痞的横行霸道,危及社会安宁等现象采取措施,严加取缔。希望新闻界大力支持,并请大家提意见。最后,有几个记者提了意见,大都集中在流氓打架闹事的问题上。这次招待会,对新闻界总算是把误会解释清楚了,但吴贞他们并不就此罢休。后来,在李良荣任省主席时,他们想搞倒我,由吴贞取而代之。这是后事,暂且不谈。
2、巩固社会秩序的几项措施
由于特务、流氓、土匪在地方上为非作歹,走私、贩毒、抢劫、绑票、打架和闹事,造成厦门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市民一夕数惊!为了巩固社会秩序,警察局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遏止。
取缔流氓打架闹事
厦门有草仔垵、和凤宫、城内、关仔内、大王、二王等角头流氓,以及陈、吴、纪三姓的封建把头势力等等,派系虽多,但都由中统或军统从中控制。他们占据角落,以欺压市民,包庇烟、赌,敲诈勒索和走私、贩毒为生。他们经常在茶楼、酒馆、舞场、戏院等公共场所,打架闹事,甚至白昼在大街上开枪射击,危及社会安宁,治安问题严重。各分局虽也曾抓几个人,但只要有头头挂个电话给局长谢桂成,马上就放走。因此流氓有恃无恐,打架闹事层出不穷,气焰嚣张至极,根本不把警察局放在眼里。我接事后了解到取缔流氓打架闹事,不仅是市民普遍的愿望,即使在警察局内部员警,亦有此要求。为了提高个人威信,我决定采取有效措施,对流氓打架闹事加以取缔。首先报请市政府批准,在警察局增设“流氓教养所”,把鼓浪屿分局的拘留所拨作该所专用,派两个可靠干部负责管理,并拟订了一个“取缔流氓打架闹事办法”,经市政府批准后实行。其内容大致规定:凡是打架闹事的双方流氓,不管任何情节,一律逮捕拘押,由警察局根据情节大小,决定处以三个月到一年的拘留,交“流氓教养所”教管,武器没收。伤害人命等刑事罪犯,则依法送法院处理。同时,鉴于过去经验(被关过的流氓了解拘留时间,最多不超过几天,而且他们有钱,在拘留所里照样可以大吃大喝,所以对警局处罚拘留毫不在意),我对“流氓教养所”管理,作了几条特别规定:流氓被拘留期间,绝对不准其家属接见、送钱、送食物。每日限定三餐粗食,并强迫打四小时石子等等。我在实行本办法之前,先向中统、军统两方面作了解释,希望他们大力支持,并能对其有关的角落流氓有所约束。而后下令各分局和刑警队,对打架闹事的流氓,一律逮捕,送局处理。如不逮捕到案,唯该管区分局长是问。
取缔流氓打架闹事办法实行后,警察局先后逮捕了流氓二十多人。其中,我所能记忆的,有两起大案。某晚九时许,海边码头附近,忽然枪声大作,一时秩序大乱,行人四处逃避。据查系和凤宫流氓吴七、余其七等人,为抢购船员私货,发生冲突。警察局刑警队会同思明分局,逮捕了其七等多人。逮捕时,其七还公然出枪拒捕。他是和凤宫流氓头目之一,与吴贞等人有密切的关系,经常到处打架闹事,是当时厦门有名的打手。逮捕其七后,我料到吴贞等人要来求情说项,为了准备和他们“讨价还价”,警察局先作一假决定,将其七等五人以“捣乱治安”罪名,送福州特种刑庭处理。当这个决定宣布时,吴贞马上打电话来约我到他那里谈话。我到他的茶行(实际上是“走私行”)时,已有陈连茂和连济民等人在座,大有对我施加集体压力之势。吴贞认为我把其七等人送福州特种刑庭处理,是小题大做,希望我从轻处理。我说,他们在大街上开枪,我这样处理,并非小题大做。并表示,案已经市政府决定,很难改变。他们提出只要不送福州特种刑庭,随我怎么处理都行。我说,为了尊重你们的情面,我只好把责任担起来,改为把他们关在“流氓教养所”,各关八个月。吴贞他们无可奈何,再没有其他意见。而我原意把其七等人关八个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另一案,是两个与中统有关的草仔垵流氓,在中山络打了一家家俱店,他们强要赊购家俱,店东不肯,就打起来。朝空开了两枪,并捣毁了部分家俱。思明分局把这两个流氓抓来后,中统方面 金水来讲请。我说,这个案本要送福州特种刑庭处理,现为了尊重中统方面的关系,只把他们在“流氓教养所”各关六个月,并赔偿一切损失和没收枪支。他也满意而去。警察局关了二十多个流氓后,市区打架闹事的事件也就逐渐减少。但所关的流氓,在我离职后不久,继任的警察局长刘树梓,陆续以每人三、五百美元赎金给放了。我有点后悔,不该帮助刘树梓发这么一笔“洋财”。
枪杀抢匪
抗战胜利后,厦门市内经常发生抢劫案件。我到厦门接事后的头两个月中,就先后发生抢案四起。一起在思明分局附近,一家金店被劫。某夜九时左右,有两名匪徒闯入该店,持枪威迫店东打开保险柜,抢走六条金条(每条十两)及其他零星首饰,劫后扬长而去。另一起,有某华侨(忘其姓名)忽于夜间失踪。据悉,系被匪徒绑去。警察局刑警队四出缉捕,均无消息。约四天后,该华侨始被放回。谈及被匪徒绑至某街一独立房屋,并勒去美钞五千元。刑警大队派队赶至该处搜捕,结果,该屋空无一人,匪徒早已逃走无踪。不久,李良荣来闽主政,他在未就职前先到厦门,住省银行里,我和他谈到厦门不断发生抢案时,他要我限期破案,并指示抓到后就地枪决,以杀抢风。
一九四八年十月左右,刑警队抓到绑架华侨案匪徒三人,供认绑架华侨勒赎五千美元不讳。我命令刑警队长宋子岑,将三名匪徒于翌日清晨三时左右,押至码头附近空地枪杀,并以押解取赃,逃跑追捕时击毙,向警察局报案。当时,宋子岑颇有顾虑。我说,这是李良荣的命令,非执行不可,他在我威迫之下,不得不勉强答应。不料第二天,宋子岑并没有执行。找他前来询问时,他说,这个案情复杂,他不敢负责,再三请求送局处理。我见他不敢执行,只好由警察局移送法院处理。后来,经法院判处徒刑,送到凤屿监狱执行。不到两个月,即听说“越狱”逃走。据事后了解,这个绑票案与和凤宫流氓有关,刑警队破案后,军统方面即找宋子岑说情,宋害怕麻烦,故不敢执行枪杀。
宋子岑不能执行我的命令,引起警察局部分干部不满。因此,我决定此后知再抓到抢匪,交开元分局负责处理。约一个月后,刑警队又破一案,逮捕抢劫金店匪徒一人,供称过去当过兵,退伍后潜居厦门行抢并供认抢金铺黄金六条及零星饰物,由三人均分不讳。我命令刑警队将全案移送开元分局负责“侦讯”。当夜即派员警将该犯押至开元路某处,执行抢杀,向警察局伪报以押赴取赃途中逃跑格杀备案。警察局据报后,照一般办案手续,通知法院验尸、各报记者都到现场拍照,刊于报端,并以大字标题发表警察局,破案经过。
取缔烟、赌
取缔烟、赌,也是警察局重要工作之一。当时,厦门市内鸦片烟馆林立,赌场到处都有。这些烟馆、赌场,多与特务、流氓勾结,得到他们的庇护,甚至与警察分驻所或分局亦多有关系。就我当时了解,思明分局长安尚志,每月由各赌场抽收所谓“津贴”,为数不少。难怪我下令取缔烟、赌之后,各分局抓的烟犯倒不少、送局处理的人数,不下数百人之多。但取缔赌场极少,特别在思明分局范围内的赌场最多,有几个赌场规漠很大。内部设有:“番摊”、“牌九”、“麻将”和“扑克”等赌具,每日聚赌的人数多至数十人。胜负均以黄金、美钞、港币计算。赌窟里有鸦片烟供人抽吸,有餐主供人吃喝,可说是应有尽有。我曾找思明分局长安尚志谈话。我说:“听说你从赌场中得到不少的'津贴?,这是过去的事,我不追究。但今后如再继续搞下去,我就不答应。为了表明你的态度,希望你把思明分局范围内的几个大赌场,全部封掉,不管这些赌场的背景是谁。我准许你可以不抓人,但要把赌场封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我就要老账新算。”经我这么一威胁,安尚志回去后,就封掉了四个大赌场,并将内部设备,如家俱等没收了一大批,送局处理。接着,各分局亦陆续取缔不少赌场。但厦门的赌风并未因此有所减退,只不过把半公开的形式转为隐蔽罢了。
3、执行金融管制政策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政府为了进--步向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迫人民将所有的黄金、外币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同时,颁布金融管制条例,规定私人所有的黄金、外币,限三个月内向中央银行兑换,逾期不兑换者,查出后,全部没收充公,并根据情节轻重,送交特种刑庭判处徒刑。金融管制办法,首先在上海、南京雷厉风行,厦门是外币流通最广最多的城市之一,国民政府中枢特别重视,曾三令五申地要市政府严厉执行。在厦门市政府成立了一个金融管制委员会,以中央银行、商会、警局、市府社会科等领导为委员,市长黄天爵为主任委员。下设文书、宣传、取缔等组。警察局负责取缔组,先取缔市面黄金、外币的买卖和使用,以及外汇业务等。并组织了五个检查队,由各分局长和刑警队长分任队长,调了大批员警为队员,不分昼夜地分赴市区各处巡回监视或检查。另外,为了防止检查队执行不力或发生流弊,又组织了一个秘密监察组,由督察长王福青负责,暗中监视各检查队,向我汇报情况。这么一来,各检查队便更加疯狂,检查人员随时进入金店、钱庄、以及各商号,甚至私人住宅亦进行严密的检查。如检查账簿有无记载黄金、外币和外汇,检查钱柜有无黄金、外币等等,一时弄得人心惶徨。
在严厉执行金融管制之后,一般正当商人和市民都不敢违犯,忍受惨重损失。对一些流氓、特务等不法奸商,则造成了他们发财致富的大好机会。他们私设电台,暗中与香港、上海等地联络通讯,交换经济情报,以便于他们所开设的“地下钱庄”进行黄金、外币及外汇的买卖活动,甚至每日派出大批流氓,在中山路、镇邦路交叉路口一带秘密交易等等。我为了有效地打击黄金、外币和外汇的买卖活动,决定先从取缔“地下钱庄”和“地下电台”两方面同时下手。根据当时调查的情况,“地下钱庄”就有三十多家(个人搞黄金、外币买卖者除外),他们未经政府许可只在门口挂一个普通商号的牌子,内部干着黄金、外币和外汇的买卖勾当。“地下电台”也有好几个,他们利用公开机关单位掩护,暗中与香港、上海等地联络通讯,互相交换经济情报,每日将所收到香港、上海的“行情”,派专人秘密传送,按周向“地下钱庄”收取电报费二、三十美元不等。一个“地下电台”每月可收到电报费达千余美元以上。我曾利用他们内部分赃不均的矛盾,找到线索,破获了两个“地下电台”。一个是军统人员、三青团干事长郭薰风掩护的“地下电台”,设在三青团分团三楼上的《青年日报》社内。我派人秘密进行搜查时,电务员已脱逃,在其室内搜出电台一部,及与香港、上海通报底稿一批,带局处理。后查明,被逃去的电务员系水警分局的电务员刘醒吾,他同时兼任《青年日报》和中央通讯社两处的电务工作。我要水警分局长刘长泗交人,他却推说刘已逃走。同时,郭薰风和中央通讯社特派员冯文质两人找我说情,我才没有追究。另一个是军统人员吴贞,利用中国经济通讯社掩护的“地下电台”。我派人进去检查,搜出两部电台和与香港、上海通报底稿。检查人员发现这个电台的背景是吴贞,不敢带人,只把两部电台和通报底稿带回报告。当夜,吴贞就托张廷标来找我,希望不要把事态扩大,要求发还电台。我佯称,这是执行军统局的命令,电台绝对不能发还。不过为了照顾“朋友”,我所能做到的,不把真实情况上报就是了。这么一说,吴贞就不敢再来麻烦了。
警察局破获这两个“地下电台”,是非常秘密进行的。中统方面了解后,认为是攻击军统的一个绝好的机会。忽于某日,在中央日报刊登一条消息,把警察局在青年日报社内破获“地下电台”的经过,全部披露出来。郭薰风见报后,马上来找我,要求警察局登报“否认”,我说:“只要青年日报登个启事声明就行了,我可负责对外绝对保密,但不便登报'否认’”。对于这两案的处理问题,我考虑到所破获的两个“地下电台”,都是军统方面所掩护的,为了照顾“自家人”军统的面子,为了避免吴贞和我的关系更恶化,我决定把这两案完全包庇下来,不向上报了事。后来,市长黄天爵曾问到此事时,我说:“我把事情办了就好了。至于此中详情,你就不必问了。”他似乎谅解我的处境,不了了之。
至于取缔“地下钱庄”,我研究只要拣几家较大的,来一个突击检查,其余的都不攻自破。我选定“茂华”、“捷胜”等五家“地下钱庄”为对象,为了怕消息外露,我决定了五个检查组的名单,以督察长王福青、行政科长吴月秋、司法科长伊扬名、保警队长林广义和思明分局长安尚志等五人为组长。各组都配备少数员警,临时电话通知到警察局集合。我召集五个组长到我的办公室来,宣布突击检查“地下钱庄”,交代检查注意要点,如黄金、外币实物,营业账簿,及所有往来的电报、信件等,并命令五个检查组于上午九时,同时出动。因为这时正是“地下钱庄”买卖闹市的时间,所以各检查组一到现场检查,马上赃证俱获。这次,计逮捕了“茂华”等五家“地下钱庄”的负责人洪炳煌等七人(其他四家行号及负责人姓名都已忘记),经警察局司法科侦讯完毕,派员警押送福州特种刑庭处理(其中两家移送厦门法院处理)。
警察局取缔了五家“地下钱庄”之后,其他所有二十余家,马上自动关门停业,厦门的黄金、外币及外汇的买卖,亦随着暂时敛迹。这就迫使市民不得不将黄金、外币,转向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使用。不久,金圆券迅速贬值,市民所蒙受的惨重损失,简直无法估计。而中央却认为此次大搜括,以厦门收兑黄金、外币最有“成绩”。除上海外,厦门收兑的外币数额,为全国第二位,并对厦门金融管制委员会大为“嘉奖”。
4、执行限价政策
金圆券发行后不久,政府为了稳定币值,决定采取人为的办法,实行所谓限价政策,通令严厉执行。厦门市政府接到命令后,决定在原来金融管制委员会组织的基础上,进一步贯彻限价政策。首先由市长黄天爵召集各行、各业公会负责人开会,宣布从当日起实行限价,限定各种物价,以当日的牌价为最高价格,只许减价不准涨价,并规定各商店,在陈列的商品上,一律悬挂牌价,即所谓“明码实价”进行买卖。如有违反限价者,一经查出,即根据情节轻重,科以罚金,没收货物,停止营业或逮捕其负责人,送法院判处徒刑等。
限价开始,警察局仍担任取缔组,组织了十多个检查小组,分局负责检查各行、各业有无违反限价规定,并随时对违反限价者,予以取缔。在实行限价初期,金圆券暂时稳定,故一般物价,尚能维持在限定的价格水平上。但是不到一个月,金圆券便开始贬值,市场上物价亦跟着波动。眼见这个限价的“堤坝”,顷刻就要“溃决”;可是市政府一再转奉上级命令,要警察局采取严厉手段,强制维持,不得突破限价。我明知物价的波动,完全由于大量发行货币所引起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必然结果,要想人为的控制限价,已完全不可能。但是我仍然坚决执行命令,决定在几种主要物资的价格上,试行控制。如棉花、棉纱、棉布、粮食和鱼、肉市场等。警察局先出动了几个检查组,会同中央银行,检查全市的各银行仓库及各大布店仓库,把花、纱、布三种物资加以登记并冻结,以防止其逃避运走。同时,全力控制粮食市场,召集粮食公会负责人到警察局开会。我对他们进行威胁恫吓,要他们具结保证,粮食不超过限价,否则就要“依法”逮捕,送特种刑庭讯办。对于鱼、肉市场,则采取直接取缔办法。警察局各检查组分区出动检查,见有违反限价的鱼、肉商就抓,在一个星期当中,逮捕了二十多人,一律送法院处理。这种强制执行限价的结果,迫使商民不得不把所存的物资,暗中分散转移。同时,内陆物资来源,特别是粮食来源,几乎完全断绝。全市各商店十室九空,小菜市场鱼、肉绝迹,造成厦门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惨景!因此,厦门的限价,仅不过维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便随着金圆券的崩溃而完全破产。
5、对付厦大学生游行请愿
厦门公教人员的食粮,向由田粮处厦门办事处按月照定量供应。厦大学生的食粮,亦在供应之列。可是田粮处厦门办事处主任沈可发,借口内陆调运不及,从不照量供应厦大学生。以致逐月积累下来,欠发将达两个月之多,经厦大总务处派人一再交涉,均无结果。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左右,省田粮处处长陈拱北来厦门视察,住厦大旅社里,厦大学生闻讯后,决定来一次游行请愿,要求补发欠粮。事先,我已得到报告。翌日清晨,厦港警察分局长电话报告,说厦大学生正在集合,准备前往厦大旅社请愿,请示如何应付?我指示他说:“他们为了食粮问题请愿,我们不要干涉,只派便衣员警,沿途暗中监视,但绝对避免与学生发生任何冲突。”一面我又以同样的指示,要督察处和思明分局严密注意。而后我跑到厦大旅社找陈拱北,当我告诉他以上情况时,他十分惊慌,急想离开旅社,避与学生见面。我说,逃避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可能引起事态的扩大。我问他,仓库里还有多少存粮?他说,只有二百多包,并且是准备发给军警单位的。我说,为了防止学生“闹事”,只有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补发欠粮。至于军警的食粮可暂压一下,我负责没有问题。但陈拱北似尚有顾虑而迟疑不决。我说:“学生请愿的目的是为了要粮,你答应发清欠粮、不是把问题解决吗?我想绝不会再发生任何问题。同时,我派人暗中保护你,你尽可放心。”经我这么一说,他才勉强地接受了我的意见。当厦大学生队伍到达旅社时,陈拱北出来与学生代表接谈。他说:“我此次来厦门,就是为了解决厦门粮食供应问题,对厦大同学的食粮,已决定如数清发,并命令粮食办事处保证今后全部供应,不得短欠。请同学们回校上课。”等语,请愿的学生见目的已达,乃整队沿原路返回学校。
6、查扣军火走私案
警察局对走私问题,向来不闻不问,一则因为走私多由海上而来,海关、水警查缉走私,负有专责,陆警不便插手,再则走私活动,都有特务、流氓为背景,抓到私货,颇有麻烦,因此警察局也不敢过问。一九四八年九月左右,市长黄天爵找我,出示旅菲律宾国民党支部一份电报,大意谓“据报东日由马尼拉开出的万福士轮船中,有共产党人偷运大批军火到厦门进口,希即查扣”等语。黄天爵要我派警查缉。我派警察局司法科长伊扬名和保警队长林广义两人,率带员警会同水警分局上船检查。到达时,船上统一检查已告结束,旅客亦正在纷纷下船。在这情况下,警局人员考虑,如要重新检查,不但旅容意见很大,而且在旅客拥挤落船中,亦无法着手,因此只好在船上暗中巡察。当巡察第三层船仓时,看到仓面放有三个大行李包,无人看管;查问,亦无人承认。伊扬名等打开行李检查,发现三个行李包中,满装军火,计有美制短枪一百四十多支。这时,适有菲律宾华侨血干团(在水仙路设有办事处负责人为周冰心)一个干事陈某走来,私向伊扬名说情,伊认为此人大有可疑,将其扣留。可是忽然有一宪兵排长,带宪兵十余人赶到船上,气势汹汹地说,这批军火系宪兵所查缉,警察局无权过问。并在警察人员疏忽中,将所有扣留的人犯抢走,带往宪兵连部。同时,还要把查扣的军火,全部运走。当时,警察人员见宪兵这样蛮不讲理,十分愤怒,坚持不肯让其运去。于是两方大吵大闹,宪兵甚至拿出枪来恫吓,警察人员亦不示弱,抽出枪来对抗。正在这争持不下,一场火拼一触即发之顷,刚好市长黄天爵在海边某餐馆闻讯,立即打电话找宪兵营长交涉。结果,决定由宪兵营部打收条,将所扣军火领去。一场火拼,才告避免。警察局将查获军火经过报告市政府,转报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司令部决定全部没收。并电令宪兵营将扣留的军火,送交该部接收。关于这批军火走私的内情,事后查出,系宪兵连与某些华侨勾结,由菲律宾走私军火进口,已非一次。他们打通了海关和水警的关节,每次走私进口,都极顺利。不料此次由于华侨内部分赃不均,有人向旅菲律宾国民党部告密,致有此价值三万美元的巨大损失。当警察局查出这批军火时,在船上的宪兵马上回去报告,宪兵连唯恐事机败露,所以派人上船,先将警察局扣留人犯抢走,翌日,即掩护其搭乘飞机,逃往香港,以此灭口。
7、取缔外轮杀价
抗战胜利后,常川厦门、香港以及南洋各地船只,均系外国商船。他们平时任意抬高票价,市政府放任自流,从不过问。一九四八年八月左右,上海联华航业公司派蔡某来厦门设立办事处,联华客轮随即加入厦门、香港及南洋航线航行。联华轮吨位八千余吨,内部舱位设备较好,而且又是旧中国历史上仅有的第一艘定期航行南洋的客轮,所以很受华侨旅客的欢迎。每次航行,都是客满,开航以来,获利甚厚。可是外国轮船公司眼红,他们想打垮联华轮,以遂其独占航业的目的,便采取穷凶极恶的办法——一致杀价。第一次将全程票价,忽然降低四分之一,并提高购票佣金,由百分之五提到百分之十。(华侨在厦门多住客栈,购买船票由客栈代办,各次班轮的船票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操在客栈的手中,各外轮为拉拢客栈购票,一律给予照船票价百分之五的佣金)联华航业公司遭到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感到相当沉重,为了继续维持联华轮的航行,不得不随着降低票价。但是各外轮并不就此罢手,他们在下班船期时,又宣布第二次降价四分之一,即两次约降低原价百分之五十。这么一来,联华轮便再也无力与之竞争了。某日,省政府顾问石西卓和联华轮经理蔡某来找我,要求警察局采取有效办法,予以取缔。我表示尽力支持。马上派督察长王福清找旅栈公会负责人来谈话,先向他们说明外轮以杀价来排挤联华轮的情况,而后强令其保证以第一次降价的票价维持联华轮本班期的客载。一面由警察局司法科,传讯太古轮船公司英人经理(当时各轮的业务,都由太古公司代理),要他具结保证,今后不再增加票价,否则将受到破坏正当航业的法律处分。这个英国人见要他具结保证颇为慌张,连说,要回去与华人经理(中国买办)商量,但为司法科长伊扬名所拒绝,坚持要他签字,两人僵持达两小时之久。实际上,是故意给他麻烦了两小时,才答应他回去,并限他两日内来局,办理具结手续。
太古公司经理回去以后,马上把船票回复到第一次降低的价格。同时,他去找市长黄天爵大发牢骚,说警察局对他不礼貌,把他软禁了了两小时,请求市长设法制止。黄天爵对他敷衍一番,而后找我,再三叮嘱不要弄得太过火了,恐引起外交上的麻烦。我也认为适可而止就行了,虽然后来司法科长还通知太古公司前来办理具结手续,但英国人没有来,只派来中国经理(买办)再三解释,请求免办具结手续,只口头上保证,此后不再随意增加票价。自后,警察局也就不了了之,而联华轮亦感到仅维持第一次降价的标准,无利可图,后来放弃了南洋各地航线,改航厦门、香港、基隆之间,南洋航线前,仍由外轮所独占。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万店优配,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
实倍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