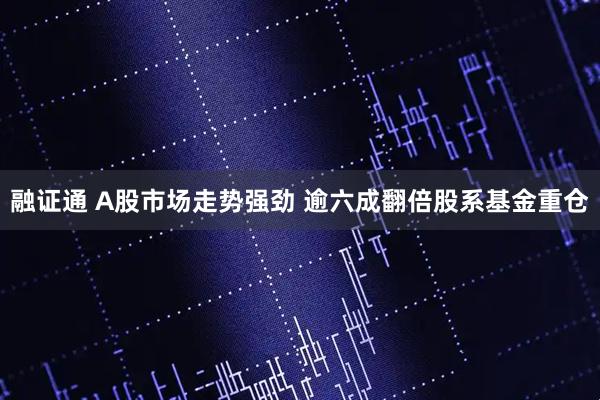华锋优配网
《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刘进宝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
中国敦煌学者一直难以忘怀陈寅恪先生曾说过的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文物是我国文化至宝,但发现以后,先后被英、法、俄、日等国劫掠而去,形成今天敦煌文物分散于世界各地的局面。罗振玉曾以“极可喜、可恨、可悲”来形容敦煌文献的发现与流散。刘进宝教授的《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在吸收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丰富的史料真实再现了这段令人扼腕叹息的敦煌文献流散史。
一、遭到劫掠的大多是精华中的精华
敦煌文物中,被西方列强劫掠而去的大多是精华中的精华。本书作者以专业敦煌学者的视角,深入剖析外流敦煌文物的文化价值与学术价值,对劫掠者造成我国文化重大损失表达了愤慨之情。
作者指出,从学术角度来看,伯希和选取敦煌文书有其独到眼光,他注重选择《大藏经》未收的佛教文献、带有年代的文书,以及非汉语文书。敦煌遗书中佛教文献约占90%以上,而具有较大研究价值的非佛教文献数量很少,伯希和盗取的敦煌写卷中,非佛教文献占比却很大。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95%以上为佛经写卷,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卷中,佛经仅占65%左右。敦煌文书中有纪年的写卷研究价值相对较大,这部分写卷本就不多,却大部分为伯希和所得。伯希和所得卷子,标有年月的卷子占19%,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这一比例仅占0.58%。(《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第120-121页,下引本书仅注页码)
英国藏西域敦煌文物包括2万多件汉文文书,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研究价值突出的民族语言文字类文书,其中包括西夏文文书6000件、于阗语文书50卷、藏文文书3100卷、吐火罗语文书1300件、粟特语文书150件、突厥回鹘语文书400卷,梵文、婆罗谜文、佉卢文文书约7000件。(第74页)
除了总体介绍英、法、俄、日等国所藏敦煌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外,作者还对许多域外敦煌文物精品逐一介绍,不仅详细介绍其物理形态、学术价值,还配有很多高清彩图,一件一件,如数家珍。如现藏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编号为Or.8210/P.2的唐咸通九年(868)雕版印刷《金刚经》华锋优配网,是我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有纪年的雕版印刷品和版画作品,作者将卷首画、经文、刊刻者题名三部分详细介绍后,用15幅高清晰度的彩图直观展现出该卷的精美绝伦,并指出“这件印刷经文,刻板面积大,雕刻精美,线条精细有力,字体苍劲厚重,墨色清晰鲜明,说明当时印刷技术已逐渐成熟”(第97页)。
有些探险者在劫掠敦煌文物时,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很多文物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魔鬼”的美国人兰登·华尔纳采用胶布粘贴的方式剥离了12幅敦煌壁画。根据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的调查,华尔纳从莫高窟盗窃精美壁画共26方,总计32006平方厘米。(第240页)由于剥离壁画时使用大量化学物质,导致12幅壁画中,有8幅受损严重,不能在博物馆展出。除了这12幅以外,华尔纳在盗劫过程中还破坏了很多壁画,在使用胶布粘贴之前,他最初计划用钢片铲刀窃取壁画,没有得逞,但这一试验毁坏了好几方壁画。被华尔纳所破坏、盗劫的壁画,大部分是敦煌艺术中最优秀的代表作品。(第241页)作者用“被华尔纳破坏的敦煌壁画(莫高窟第323窟南壁)”“莫高窟第323窟南壁被华尔纳切割去的部分”“莫高窟第323窟南壁复原图”这三幅插图,直观清晰地反映了华尔纳对敦煌壁画造成的伤害。曾在莫高窟考察的向达先生痛斥华尔纳“将千佛洞的壁画一幅一方的粘去或剥离,以致大好的千佛洞弄得疮痍满目”(向达《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此外,日本人大谷光瑞考察团文物保护意识不强,橘瑞超在考察过程中打碎过泥塑佛像。(第185页)
面对全书所收近百幅外流敦煌文物的照片,以及作者对每件珍宝的详细介绍,不由得使人感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辉煌,同时对外国探险家的劫掠和破坏无限愤慨。
二、文物主权意识的觉醒
是什么造成了敦煌文物的外流?“外国探险家、考察家在中国的考察活动,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作者将敦煌文物外流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观察,一语道出了敦煌文物外流的根本原因。从晚清到民国,西方列强在中国掀起你争我抢的侵略瓜分狂潮,对中国文物的巧取豪夺就是侵略狂潮的一部分。与政治、经济侵略一样,西方列强对文物古迹的考察也划分“势力范围”,如德国与英国约定:“对于中国境内的遗址的挖掘,双方应利益均得。德国远征队的活动范围限定在吐鲁番一带,而库车一带则属于俄国远征队的活动范围。”(第266—267页)斯坦因直白地将国家之间的竞争作为自己考察的理由,他声称:“我敢肯定,和阗和中国新疆南部是英国考察的适当范围。用现代术语说来,它按理是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而且我们也不该让外人夺去本应属于我们的荣誉。”(第266页)
此外,当时政府的昏聩无能、地方官吏及下层人士的愚昧无知、文物主权和保护意识的缺乏,都是造成敦煌文物被劫掠外流的重要原因。尤其使人痛心的是,上到官僚士大夫,下到平民百姓,不懂文物艺术及其价值,对敦煌文物的外流漠然视之,毫不关心,甚至充当了文物外流的帮凶。曾任甘肃学政的著名学者叶昌炽,早在1903年12月就通过敦煌县令汪宗翰得知敦煌发现藏经洞文物的事,并得到汪宗翰赠送的藏经洞所出佛画、写经,但从未想到去敦煌看看。以至于在1910年1月23日的日记中,痛心自责:“中国守土之吏,熟视无睹。鄙人行部至酒泉,未出嘉峪关,相距不过千里,已闻其室发现事,亦得画像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室藏,輏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叶昌炽《缘督庐日记》)
英法等列强窃取敦煌宝藏的消息引起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对文物外流的关注。“五四”以后,由于反帝爱国运动不断高涨,中国社会,首先是知识阶层,逐渐产生了文物主权意识。1925年,华尔纳第二次到敦煌时,就明显感觉到中国社会文物保护意识的觉醒。敦煌县政府坚决不同意考察团住在千佛洞,并规定考察团必须接受群众监管,不得触毁壁画及其他一切文物。华尔纳抱怨说:“有十多个村民放下他们日常的工作,从大约十五里之外的地方跑来监视我们的行动。”(第238页)正是敦煌地方政府和当地民众的努力,才使得华尔纳再度大规模盗窃敦煌壁画的阴谋没有得逞。
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来华考察。为避免文物外流,北京大学发起,联合12家机构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协会章程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考察,应以参加中国学术团体或机关考察团的方式进行,不得自行调查采集,“凡采集所得,均应归国内学术机关或团体,以供内外国人之研究”(《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章程》,刊于《东方杂志》24卷8号,1927年)。经过谈判,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签订协议,规定包括所得古物“统须交与中国团长或其所委托之中国团员运归本会保存”等19项条款,保证了考察所得文物全部留在中国。(275-276页)1930年4月底,斯坦因再来中国,前往新疆偷挖文物,便被中国政府取消通行证,没收盗掘文物,监视出境。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古物保存法》,明确规定“埋藏地下及由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归国有”,这是中国政府制定的第一个保护文物、维护文物主权的法规,标志着全社会文物主权意识的强化。(274页)
三、流散文物的“回归”
敦煌文献流散各国的局面,使得敦煌学研究从其开端就具有国际性,各国学者致力于敦煌学研究,使其成为国际显学。作者虽然痛恨敦煌文献外流所造成的文化损失,但并没有因此而否定英、法、日等国在敦煌学上取得的成绩。如伯希和,作者认为他在敦煌“劫经”,完全是强盗的角色,但他在世界东方学研究上做出的贡献,又使其成为受世人敬仰的著名学者,也肯定了他长期与中国学者保持友好交往,帮助中国学者阅览法藏敦煌文献及各类古籍。(第122页)对于日本学界推出的《西域文化研究》6卷7册,以及《大谷文书集成》4卷,作者也充分肯定了其学术价值,及其为中国学者提供借鉴参考的意义。
作者对开展敦煌学研究的国际平等合作也持肯定的态度。作者详细介绍了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等人提出整理出版俄藏敦煌艺术品,经过多次协商,1993年签订出版协议,又经过敦煌研究院段文杰、樊锦诗等先生的指导,最终在1997-200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俄藏敦煌艺术品》全五卷,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全面了解俄藏敦煌艺术品。(第206页)此外,英藏、法藏、俄藏敦煌文献图版的整理出版,都是国际合作的重要成果。
今年5月,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向我国返还了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占》,得到我国社会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振奋之余,不由引人思考敦煌文献的回归问题。作者在本书《结束语》中提出,在目前无法实现实物回归的情况下,可以先实现敦煌文献彩色照片的回归,“凭借现代科学技术和印刷条件,用彩色高清图片的方式印制保存,实现流散文物一定程度上的‘回归’”。
结语
为什么要触碰敦煌文物流散这一沉重的话题?作者认为,了解敦煌文献的流散情况,“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的把握,对未来的认识”(第286页)。敦煌文献被劫往海外已经一百年了,每个中国人都在期盼敦煌文物的回归,但这是一个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首先就要弄清楚这个难题是如何产生的,《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就是直面这个问题的。本书图文并茂、引用大量史料,真实再现这段伤心史,警示国人牢记历史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有很好的社会意义。
(作者:赵大旺)
华锋优配网
实倍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